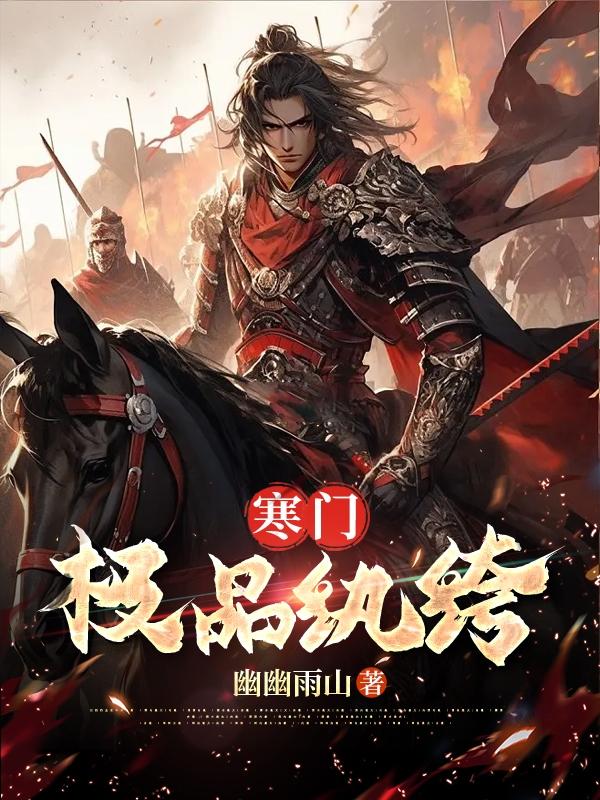乐文小说>纨绔皇子:先创六宫再夺嫡 > 第286章 率滨其人(第1页)
第286章 率滨其人(第1页)
寒潭先生只是笑了笑,而后对着他的观众们说道:“这位小友的学识不低呀,且也非是在开玩笑,其之所言皆为真实,并无虚妄。论语之中的确是有一句‘易易云者三日’,只不过这句话不在你们现在所读的论语之中,而是在齐论语里。礼部沈尚书曾得到一张写着齐论语知道篇的只言片语,此时正收藏于其家宅之内呢!”
寒潭先生话一说完,众人皆为哗然,但很快就又平静了一下去。
寒潭先生接着对玉面书生问道:“老夫与沈尚书乃为故交,来长安之后他自是拿来给我看过。小友即非姓沈,看你这年纪应该也不是能与沈尚书交上朋友之人呀?莫不是他的学生?这也不对,沈尚书为人谦和,是教不出你这样豪气之人的。老夫想问一问,你是如何知晓那齐论语之篇目的?”
玉面书生轻狂地笑道:“那张纸可不是沈礼部自己变出来的!”
“是率滨先生所书,字迹老夫看过,并无出入。”
“你即言我非沈家人更非其学生,这不是一目了然么?除了我率滨,还有谁人能写?那字即是我所写的,我又如何会不省得?”
玉面书生话一说出口,原本安静下来的众学子们再度哗然了起来。
寒潭先生皱着眉头打量了一下眼前的玉面书生,疑问道:“你是率滨?”
玉面书生笑道:“我自是率滨先生,这有什么好疑问的?若非如此,谁还能知道什么齐论语?怕是在坐的众位即使再读个三十年书,怕也未及我现在学识的一半呀!”
众人对这玉面书生即是生气,又是畏惧。
生气的是这人不只是不把寒潭先生放在眼里,就连在场的众位好似也都不屑一顾。
畏惧的是,眼前人要真是率滨先生,万一与对方争执起来,怕是以自己现在的学识只会自取其辱。
玉面书生刚要说话,鼻中便闻到了一股酒香味。
她转头一看,只见得一个身形极为飘逸的酒仙站在了自己的边。
那“酒仙”正是之前与玉面书生搭过话的山滔。
山滔一边将酒葫芦系在腰间,一边打量着那玉面书生,而后嗤笑了起来。
玉面书生生气地说道:“你这是笑的什么劲,有你什么事?”
山滔笑道:“我草字曼益,年长于你,你叫我一声曼益兄不算是吃亏。”
“什么满不满意的,我又不识得你,要你在这里多嘴,谁又愿意叫你什么兄长?我之兄长才高八斗、状元之才,你还不配!”
山滔笑道:“在场若是有人会下棋,怕不会对我这个名字感到陌生。我非是他人,乃是长安城最大棋社黑白银勾院的大掌柜。”
“原来是那现世阎魔一伙,难怪了。看你流里流气的,果然不是什么好人!”
山滔呵呵笑道:“率滨先生言语犀利、作风乖张……”
“用不着你在此评价于我,你也不配来与我言说。”
“小兄弟,我不是在评价你,我说的是率滨先生。”
“我即是呀!”
“你?呵呵。率滨先生是傲气非常,也对有些人也极为不逊。但对有真本事之人,比如寒潭先生却是极为礼貌的。且他原即是六爷的座上宾呀!你即是说与六爷往来之人皆无甚好人,那你亦不是什么好人了吧?”
那玉面书生冷笑一声说道:“我也没说我是什么好人呀?”
山滔说:“我与率滨先生同是六爷座上宾,我可是见过他的!你刚刚却说自己不认识我,这且不是很可笑么?”
玉面书生愣了一下,好似明白了这里面的逻辑错误。
寒潭先生见得自己儿子出来给自己解围心中自是高兴。
他自来到长安城找儿子,就没与山滔说过几句话。
趁着这个机会,他连忙对山滔问道:“此人不是率滨么?”
山滔摇头答道:“率滨先生的确也只有二十岁上下,那嘴也是变着花样的见谁损谁,但他却不是率滨先生。”
玉面书生言道:“见过我之人未必只有六爷手下,还有我父母亲人呢。没见过我的诸如在场的众位,我看也未是六爷手下吧?你想能证明什么?”
山滔笑道:“只问你一件事情。你即是六爷坐上宾必然知晓五叶庄里的酒窖现在还有多少酒吧?”
玉面书生愣了一下,那眉宇间透出一股古灵精贵的神情之后说道:“我又不好酒,不像你似的,如何会晓他五叶庄里有什么?”
山滔笑道:“只要是你率滨先生就一定会知道!因为六爷为了防我偷他酒喝把身子喝垮,一早就把庄里的酒给摆空了,所以现在五叶庄里是一坛酒也没有!”
“我有些日子没去五叶庄了!”
山滔又笑问道:“那你至少该知道五叶庄之名典出何处吧?”
“什么?”